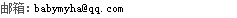成熟
妈咪爱婴网 www.baby611.com 2006年12月09日 11:43:29
第一根灰色的头发冒出来,混进我中年的秀发时,我让儿子帮我拨掉。等到一整撮银色的头发长出来时,我要儿子不要再拨了,那已经跟他儿时的古灵精怪一样,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曾经为了我穿着破旧休闲鞋参加家长会,感到尴尬。然后,我准他到树屋过夜。刺耳的音乐衬托下,宽松的裤子像洋葱皮一样,一层层剥开。在匆匆迈向成熟的岁月中,日落和季节交替滑入地平线。
我儿子的船此时正在中国海。他未婚妻的祖母打电话来告诉我,他们解除婚约了。我看着铜版的邀请函,深蓝色的字体印在白色的纸上,正好拱配他的制服。塞在旁边的是一张15年前的全家福照片,可以看到他小男孩的脸蛋在一整群嘻笑的姐妹中间游水。
我本想能保护他。就像以前,他自尊心因为失败或老师打击而瓦解时一样。我看到,他摇摇欲坠的天平这几年好不容易平衡下来,即将有光明的前途,现在却遭到恶棍的破坏。这个学生的消息让我感到愤怒,那个不怀好意的祖母把我丢到飓风中心,无端的臆测加速蔓延扩大。我运用在消除压力课程学来的招数,深深吸了一口气,头慢慢转圈,消除我颈部肌肉的紧张。
记得生他的时候是早上10点零4分,我在杂货店的羊水破了。他父亲紧张得连助理生产课的后半段都没上。往事急电般爬上阴冷的墙壁。深深吸了一口气。随它去吧。幻影慢慢消散。
几分钟后我的前夫打电话来说,他也接到了电话。他说,长久来看,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时一股暖意袭来,总算有人和你一起担心你的孩子,两人一起保护他。我们决定分别立刻写信给他。前夫又加了一句说,秘密总是有力量占据人生的阴暗面,他那平静的语气外带一丝笑声,像一阵冷飕飕的风从电话线传过来。
我的信写得简短,鼓励的成分居多。虽然我厌恶给成年的孩子任何劝告,还是忍不住建议他立刻联络他的未婚妻。不过才28行的信,我却写了两个钟头。孩子那卷发年轻的影像宛如潮水般不断涌来,把我从目的地冲走。在温柔的回忆中,两岁的他张着充满信任眼神望着我,向往着拥有口琴。孩子充满信心凝视着我,那好像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感谢上帝给我这个礼物。我一直想变成他的朋友,这所有愚蠢的计划在他表少年的强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到他长大成人,转了一个圈,这个梦想才实现。现在根基稳固,我赢取了他的尊敬和友情。到底我是怎样的母亲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永远是他的母亲。
最感动的还是他说过的话,不是他得到的学位或奖项。那些信件、电话、说过的故事,鼓舞着我自信地顶着我灰白的头发。
去年上课时,一位士官要求每个海军击战队员站起来介绍自己的名字。我儿子站起来,大声说:“报告长官,我叫亚伯(译注:《圣经故事》里亚伯是亚当的次子,被史长该隐所杀)。”
士官回答道:“下士,这算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长官。”亚伯答道。
“你父母在怀你时,一定是嗑药嗑昏了头。”
“报告长官,没错。”亚伯答道。
想到全班哄堂大笑,士官努力维持秩序的窘境,我不禁咧嘴笑了出来。从一个学步的孩子到一个英挺的海军;从牙牙学语,到完全掌握语言,孩子的话是完美的。
我把信寄出的第二天,亚伯打电话告诉我,婚约解除了。一直在混乱时空中徘徊的我,这时候才知道,我们其实同一时间收到这个消息。亚伯打电话给他未婚妻的同时,他未婚妻的祖母致电给我。
年龄日渐衰老,越来越多讽刺的转折冲击着我。人生的巧合不尽是漫无章法,而是,命运向我的人生方向投掷快速球,训练我奠定根基,产生了一个有章可循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