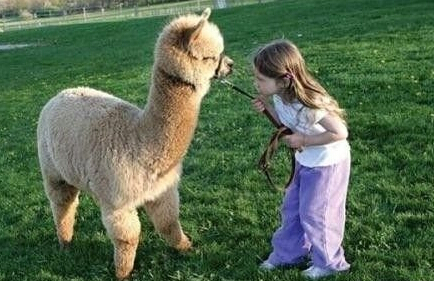感动母亲:女儿是我最完美的作品
妈咪爱婴网 www.baby611.com 2007年01月31日 12:40:49
“今天是女儿林熹的17岁生日,没错,5月7日。”胡振萍的喜气溢于言表,“只可惜我来得匆忙,还没有来得及向她祝贺。”按照思维定式,记者建议这位母亲拨打电话。胡振萍摇摇头,脸上的微笑依然在荡漾:“你忘了,她听不到的。”是的,女儿是一个双耳全聋的孩子,但是,她能够开口说话。
上天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孩子
我是驻马店正阳县的一名妇产科医生,工作中的每一天都面对呱呱落地的婴儿,捧着每一个粉嫩的初生婴儿、看着他们睁开清澈的双眼、听着第一声开天辟地的啼哭,一种想法总是忍不住浮现:每一个婴儿都是失落在人间的天使,是父母的爱引领着他们来到人世;每一个婴儿都是完美的,而最完美的将是我的,由我来创造。
26岁那年,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988年的5月7日,这个日子对于我和我的丈夫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那一天,在甜蜜的疼痛终极,透过医院产房的窗棂,我清晰地看到了暮春的晚霞,像是火焰在燃烧。那一刻,我憧憬着女儿的生命也一定像霞光一样灿烂、美丽。被包裹着抱到我面前的女儿果真是最完美的:黑油油的胎发、红艳艳的小嘴、粉嫩嫩的脸颊。恍惚之间,我竟然不敢相信我就是这个生命的制造者。
完美的女儿也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名字,我和丈夫翻阅字典,经过无数次的筛选,最后敲定了一个名字:林熹,熹就是光明的意思。我们祝愿女儿的一生如她的名字,郁郁葱葱、阳光普照。在林熹10个月之前,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偶然的鞭炮声惊醒了我们一厢情愿的美梦。那是1989年的春节,也是一个太阳落山的时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预示着新年的到来。我带着林熹远远地看热闹,当时她才刚刚10个月,还不会真正意义上的走路,需要我的双手支撑和扶持。林熹对于点燃的爆竹十分着迷,在别的孩子用小手捂住耳朵,或是吓得直往大人怀里钻的时候,她勇往直前,一点也没有显出害怕的模样,拽着我的手前进。我的女儿真的很勇敢,我自豪地任由她朝前冲,但是,她的勇敢显得有些过分,径直冲向正在炸响的鞭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我的耳边炸响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愣住了,因为我是一名医生,职业的敏感使得心头一阵震颤:莫非,莫非林熹的听力有问题?这种预感在我的心头蒙上了阴影,从此之后始终挥之不散。
当我把这个疑问说给丈夫听时,丈夫起初不以为然,他说是我当医生当得疑神疑鬼了,孩子活泼可爱,会有什么问题?我也自我安慰寄希望于年龄小的耳膜内陷,发育成熟了也许一切都正常了。后来,我有意识地猛然发出声响或是在女儿的身后敲响玩具,但是十有八九她仍然是无动于衷。
在这种阴影的笼罩下,林熹不知不觉两岁了,我和丈夫带着她来到北京同仁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经过最先进的电子扫描和最权威的专家测定后,得出的结论是“双耳全聋”。听到这个结论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世界末日,绝望、悲凉,我的眼前一黑,几乎站立不稳就要晕倒在地。支撑我的是怀中的女儿,她还在牙牙学语,小脸上是天真的笑容,嘴里发出含含糊糊的“妈妈”的声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我的孩子为什么和别人的不一样?她还没有来得及学会说话就要一辈子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吗?
胡振萍回忆起往事的时候,显得格外平静,除了渐渐消失的笑容,她的表情和语调一如湖水波澜不惊。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表面平静的湖水下激流暗藏,甚至还有棱角分明的冰山。我想,正是这样的冷静造就了坚忍不屈、从不言败的个性。
我的孩子和别的孩子没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