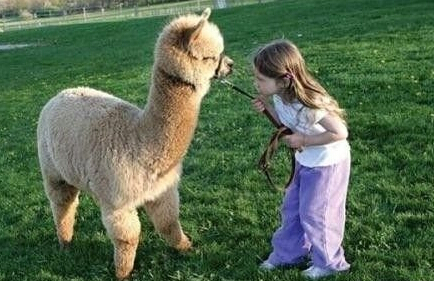感动母亲:女儿是我最完美的作品(2)
妈咪爱婴网 www.baby611.com 2007年01月31日 12:40:49
配副助听器能否改变林熹的现状?在北京同仁医院,我就曾经询问专家这个问题,不,不是询问,简直是恳求了,我几乎是恳求专家给女儿配一副助听器。我把希望寄托在助听器上了,但是,专家的回答击破了我渺茫的一丝幻想。专家说:“没有用的,助听器只是能够帮助有听力的人增强听力,而你的孩子一点听力也没有。”
那么,女儿难道说就要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吗?针对我的疑问,专家也给予了答复:虽然聋了,但是可以聋而不哑,只要进行听力语言康复培训。
哪里有这样的培训中心?专家说,“目前一些地方设置了聋儿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中心”,但是他的话锋一转,“这些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只是接收听力在70分贝以下的孩子”。
经过听力语言康复训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一直锲而不舍地询问,好像濒临淹没的人急于要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专家告诉我,即使是达到聋而不哑,就是通过看人的口型辨别发音,然后猜测人家说话的内容而与之对话,也是相当难办到的,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漫长极其需要耐心的过程,考验着教者和被教者的毅力。
曾经出现过成功的例子吗?这是我最想了解的主题。“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一例。”专家回答。
“谢谢,谢谢!”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够了,已经够了。只要有一例,我就能够使得女儿成为第二例,因为别的孩子能行,林熹就能行。
专家的话点燃了我和丈夫希望的星星之火,我们当即就带着女儿在北京的大小书店奔波,只要是和听力语言沾上边的书,我们尽收囊中,回家之时已经收罗了满满一箱子的有关书籍。常言不是说“十聋九哑”吗?我就要让女儿成为10个聋儿中那个唯一的不哑者。
从北京回来,我就按照书上写的听力康复训练方法教林熹发音,于是,每天要对着听不见的女儿说上无数句的话成了我的功课。早晨,林熹刚一睁眼,还揉着睡眼惺忪的双眼,我就一字一句、绘声绘色地告诉她:“天亮了,太阳升起来了,该起床了。”然后,穿衣、刷牙、洗脸、吃饭,每做一件事情,我就一边做着一边大声地对着女儿说上好几遍。除了这些,我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女儿“聊天”,给女儿“讲故事”。每一天都是如此,从女儿一睁眼到女儿进入梦乡,我都在不停顿地说,不知疲倦地说。由于说话太多、声音又大,我的嗓子坏了,反复肿痛、充血、沙哑。但是,我坚持下来了。
就这样,半年之后,林熹度过了最初的好奇和中途的漠然,终于对声音有了反应,也就是发出频率较高的尖叫声。这种叫声,旁人听起来是刺耳的,甚至是恐怖的,但是对我而言却是世间最动人的音乐,因为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希望之声。一天午饭后,我一如既往地给女儿进行听说训练,而林熹口渴了打着手势向我要水喝。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即把水送到她的嘴边,而是拿着水杯喊着“喝水”,一遍、两遍、三遍……百遍的呼喊过去了,林熹的干涸的嘴唇也随着我的喊声一次次一张一合,小脸一阵阵涨得通红,可是就是发不出喝水的声音。为了让女儿能够清晰地看到我的口型,我索性单腿跪在地上,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指着自己的嘴唇。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一个钟头过去了,我的膝盖由疼痛到麻木,再由麻木到疼痛,就在我几乎丧失信心,垂头丧气准备把手中的水杯给女儿的时候,耳边猛然响起了含糊不清的声音“喝———水”。我惊喜地把女儿揽在怀里,眼前一片模糊。那时,林熹两岁8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