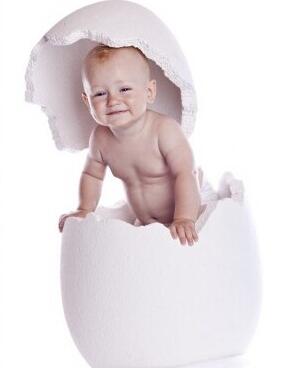真实的震撼(2)
妈咪爱婴网 www.baby611.com 2007年01月27日 11:59:05业化”和“世俗化”,势必进入异化的怪圈之中,形成对儿童健康精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专家学者对此极为忧虑并呼声强烈,教育部和文化部已开始重视并做出相关努力。
美术界具体职能部门的较少“介入”和理论的弱化和使中国儿童美术在经常意义上仍成为爱心、慈善、或某个政治活动中的点缀品,停留在文化馆、少年宫等群众文化层面及妇女儿童的特定人群,对儿童美术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没有得到普遍认知和深入探究,以致本属于儿童美术范畴的特殊教育形式被常规艺术教育的规范化模式所消解, 我们清楚意识到: 儿童美术理论滞后与深度困乏所带来的尴尬和危机将直接影响中国儿童美术事业的正常发展,作为正确构架美术教育理念和实践方式的具有学术导向性的中国儿童美术理论体系应早日形成。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儿童美术理论的基础构建已落后了数百年,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的崛起使儿童艺术首次得到高度重视,理论界的学者们从对“儿童艺术家”们浪漫式的好奇迅速发展为美学领域的深刻研究,经历了不同流派的变迁,令人尊重的传统与革新精神共同发挥作用。理论指导着教育理念的方向和实验,其结果又推动着美术理论的深化和教育纲领的演变,几百年的良性发展已在欧美国家的国民审美素质、以至整体生存环境的美感上得以体现,根据大量理论研究成果出台的 1994年《美国国家艺术教育大纲》在前言中写到: “事实上,我们依赖艺术帮助我们实现人性的完整。我们深信了解艺术和艺术实践对儿童精神思想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艺术与教育一词的含义是不可分的。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缺乏基本艺术知识的人能够表明自己受过真正的教育。”
中国美术的展览、出版和学术研究机构是否对儿童美术及教育给予过足够的关注和政策支持呢?现状令人担忧:据调查统计,目前中小学生有进入美术馆欣赏作品经历的人数比例为 1%;具有引导儿童欣赏和创作部门的美术馆屈指可数;重要的学术单位至今未见设立研究中国儿童美术理论的课题;除师范外,全国没有一所高等美术专业院校开设儿童美术工作室或研究室,而相当数量的美术教师来自专业院校,在儿童美术教学中却不得不从头开始;儿童美术读物的创作出版处在低谷境地,优秀作者大量流失、作品极度缺乏,孩子在美术读物中所能获得的美感与智慧正被西方涌入的模式化卡通、简笔化、赌博性的游戏所取代,严重损害中国儿童的心智健康,民族文化血脉的承传也面临被后殖民主义摧毁的危险。
而国际的情况是:儿童美术作为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美术专业的各个机构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以德国为例;著名美术院校已开设关于儿童美术、教育、心理的研究课题;少儿美术教师有计划地去美术学院进行美学、艺术史的在职培训与理论更新;几乎所有的官方美术馆都设有鼓励儿童鉴赏艺术和创作的职能部门,美术馆的研究人员有为孩子讲解的义务,“到美术馆去”已成为学校美术教育的基本环节之一;位于首都柏林的德国联邦青年艺术学院内 1/5的工作室和陈列空间属于儿童,孩子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创作、往来,和学院大孩子们一起展示作品,学院外的公共街区中心伫立着一块涂抹色彩的粗石就是儿童所作。该院院长是德国联邦艺术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对儿童的创作予以极大尊重,她认为:儿童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与成人作品是平等的,成人正不断从儿童作品中得到启发。此外,儿童美术读物异彩纷呈,感性的创作得益于良好的展示、签约与出版制度,使得有创作特色和民族思维个性的作者保持着童心,最终的受益者是孩子,更有益于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根基的水土保持。除德国等西方国家外,日本也在日益完善。
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已导致中国儿童美术的严重倾斜状况。一方面,西部、老少边穷等不发达地区的孩子没有美术老师和基本的材料工具;另一方面,城市儿童已被看作课外美术的强大消